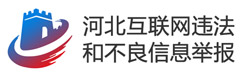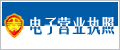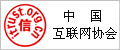G20框架下我国的国际经济金融战略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浏览:次|评论:0条 [收藏] [评论]
主持人:目前G20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格局中的地位如何?G20框架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战略机遇?张涛: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都非常深…
主持人:目前G20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格局中的地位如何?G20框架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战略机遇?
张涛: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都非常深厚,具体而言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双边关系,在我国对外事务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应该认识到,我们参与多边机制的历史也同样久远。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成员国之一,也是联合国机制下的多边机构——包括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多边机构和区域组织的成员,甚至还是有些机构的创始成员。
但是,多年来我国运用多边关系、多边机制处理国际事务的力度和范围相对双边关系而言,更多地还处于协助和配合的地位。在五十年前世界一极格局或者两极格局的情况下,处于这样的局面还能理解。而今大家对全球基本形势的判断是,虽然美国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新的冲击。多数人认为世界多极化格局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中国融入世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总的来说,世界大部分主流国家都接受了开放和全球化的基本思路。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多边经济和金融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多边国际经济金融关系和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视角,而G20则是这个视角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如何在多边国际经济金融战略的大框架下看待G20峰会?我个人参加过多伦多、首尔和戛纳三次峰会。我认为,G20峰会具有四重特殊性,一是机制化,不是不固定、临时的会议。迄今为止,G20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峰会,今年是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也排上了议程。因此,这是个机制化的论坛。二是G20没有投票机制,没有机构化。相比之下,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条约上的,而G20没有条约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投票机制,是共同协商讲求共识基础的论坛。作个通俗的比喻,它既类似于董(理)事会,又不完全是董(理)事会。三是领导人机制。相较而言,IMF既具有机制化,也有机构化的特征,但它不是领导人机制。四是G20第一次由主要新兴经济体参与的机制。参与的国家和经济体有20个,这一数量并没有经过科学界定,究竟参与国家的数量为多少会使得机制更加有效?G20的治理结构至今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基于G20的特点,在我看来,必须要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总体统筹我国对外经济金融战略。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是我们的出发点,包含了我国在所有双边、多边以及G20的机制下,要达到的总体目标。党和国家相关方针政策都对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目标进行了总体统筹和规划。在此基础之上,学术界应该更进一步地思考对外开放的现状以及前景,在拥有基本愿景的前提下,再来谈G20,恐怕会更有针对性。
第二,如何处理G20与其他多边机构、区域性组织之间的关系?由于G20是领导人机制,而对领导人谈话并没有框架限制,所以G20对主要国际多边机制比如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论坛以及WTO等均有所涉及。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绝大多数多边机构有其固有和独立的诉求和治理结构,也有自身的运作方式。在G20机制下如何协调各方利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课题。
另外,整体而言,我国在双边之间还有很多重要的对话机制。比如中美、中英和中欧战略对话等等,中日之间也有副总理层级的对话机制,还有诸如中日韩的区域性对话机制。因此,总体对外战略、G20、多边机构和双边对话机制四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协调这四个方面的关系?G20如何对其他三方面进行指导、支持、补充?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何建雄: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政治平台来推动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中国未来经济尤其是金融的发展,包括怎样在全球范围配置储蓄、寻求回报、管理风险,都与全球金融体系息息相关,因此中国希望有一个开放的全球性金融系统。从制造业角度来看,中国面临产能过剩,因此未来的发展、在价值链中的提升、相对竞争力的提高,都需要谋求开放的贸易体制、投资体制和安全可行的危机管理体制。现在已经建立了很多关于全球治理结构的机构和机制,但要使这些机构、机制有机协调,需要在最高的政治平台上来进行推动——G20就是这样一个平台。G20能够提出新的议题,重新确定已经在国际层面讨论过的议题重点,对一些已经建立的规则进行政治层面的背书。
我国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迅速发展的中国会使一些国家感受到冲击。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的角度来讲,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还很远。然而改变平衡的往往是增量。中国的增量变化在G20成员中非常突出,特别是在大宗商品需求、节能减排和国际储备等方面体现很明显。这使得国际社会聚焦中国,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关注的中心。
何帆:G20为中国到底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机会?我个人认为G20的出现为我们思考世界格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G20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按照大国来划分的世界组织,其创新之处在于把大国组织到一起,不论对方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世界的划分标准会影响对国际关系的处理:若按意识形态划分,那就是冷战的格局;若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来划分,则是另一种格局。
现在,中国则需要搞清自己的定位问题,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大国之间存在共同点,美国是个发达国家,挪威、卢森堡也是发达国家,但是美国和中国、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很可能比它和挪威、卢森堡的共同点多得多,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大国之间存在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论是自然学科还是其他学科研究国际问题,当问题足够大了以后就会发生一些质变,这一点能够启发我们思考一些新的国际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大国问题呢?一方面,我们希望与大国合作,就需要寻找新的利益交汇点。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愿意完全接受西方的理念,虽然有些观念在最后会趋向一致,但是还是有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趋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更不用说时时处处都有不同的利益,这正是为什么要讲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就是为了预防不被西化,给自己留余地。因此,我们在考虑与大国合作的时候,一方面,需要说明双方的共同点,关心的共同问题,但另一方面需要说明双方关心的角度不一致,这是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考量。
所以,G20对中国而言,就其本身可能作用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但对于我们如何认清并把握世界格局则具有深远意义,就像我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样,加入G20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中国参与G20框架的战略选择
主持人:为什么我国要参与G20的相关事务,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未来应如何通过G20平台,贯彻执行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张涛:具体而言,我认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在参与。虽然G20诞生时间不长,生命力却依旧旺盛。它也许不如最初诞生时人们的期望那么高,但其发展应是一个细水长流、绵延不绝的过程,需要我们的耐心,不能因为早时早刻没有重大结果或者闪光点,我们就不重视。在国际政治经济气候不那么积极向上的背景下,G20可能会面对很平淡的结果,不会总出现2009、2010年那样令人激动的时刻——2010年是危机时期的特殊状态。在我看来,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G20是一个第一次由新兴国家参与的经济金融协调机制,我们就一定要积极参与,并且把握好这个平台,这应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二是精心维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世界第一次把聚光灯打向中国。虽然我们的体量确实变大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早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这些聚光灯。国际多边机制可能也对聚焦中国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我们更要精心维系与多边机制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当前我们还处于多边关系发展的初级阶段,这就好比两个人从最初相识后慢慢地了解,再进一步深入发展细致和稳定的关系。我认为,一个国家与一个多边机构之间也应如此,应充分理解对方的文化思想逻辑和处事方式,只有深入其中才可能深入了解。多边机制如何运行有赖于历史的积累,单靠我们个人不可能把握所有积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关注,才能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至于人才问题。除了有良好的学历和深厚的研究能力,还应该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我们发现,有时双方无法进行良好沟通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语言——可能我们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或者汉语,但却不能很好地理解对方所表达的内涵。这方面,我们与其它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我们一定要精心维系,认真比较,长期坚持。
三是有所作为。身处这个平台,我们也要有所作为。有所作为,一方面要为我国的自身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我国也要为这个多边机制及共同利益服务。参与多边机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利用多边机制,也是为我国争取更多利益的重要方式之一。当然,在多边机制下可能需要触及多国的利益,这就需要我们恰当地把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一般利益与核心利益,单方面利益与整体利益等多种利益关系。
既然我们已经参与到多边机制中,我们就应该认真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如何从G20的视角,在G20及其他多边机构中提出我们的见解?如何在这些平台上建立中国元素?如何在多边机构中准确地进行自身定位?这是一个重要工作,但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点滴积累孕育。比如,如何在多边机制里寻找话语权,这不是简单的大体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入细致地渗入到多边机制的具体细节中,正所谓润物细无声。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握话语权。
在制订明确的长远战略框架的基础上,我们更要脚踏实地做好日常事务中的每一份工作。多边机构主要采取投票方式,增加了份额,有了多的投票权固然重要;投票之前的工作更为重要,如何掌握投票之前的主动权也极为艰难。这需要靠大量事前长期而细致的努力。否则即便有较高的份额也不能包打天下。比如,目前美国在IMF的不少重大事项中仍拥有否决权,但是也并不是每次美国的提案都能通过。许多事例表明,前期工作看不见,摸不着,但至关重要。
何建雄:中国和世界的利益在总体上是祸福相依的,开放、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对中国有利。我们在酝酿对一些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倡议时,往往会较多地考虑对方的意图。我认为,以对方意图来确定己方立场,往往会将自己放在不利的位置,受人围攻。正确的态度是应该具体分析利弊,即使对方针对我们,也可以善加利用,积极参与。除立场问题外,还有人担心一些倡议的门槛过高。我认为针对门槛过高的问题,应当采取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加。有的时候,在谈判过程中门槛可能会降低。同时,我们国家还在发展,现在看高的门槛,过几年可能就不高了。但如果开始就采取消极态度,在他国谈判成功后再寻求进入会更加困难。
我国通常很看重G20峰会和部长会,但有时真正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在会前和会外,会议已经是宣布战果的时间了,会前、会外才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要寻找利益相关方和利益共同方,寻求利益最大化。
另外,我认为国内协调可以进一步加强,部委间的协调应有充分的前瞻性。重大倡议的推动需要一年,甚至数年时间的准备。战争要赢得胜利,就要合理运用各方面力量,内部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至少参加会议的领导要清楚哪些方面要有所推动,哪些方面要有所操作,应该支持或是反对哪些议题。我认为在内部协调方面可以多做总结。
何帆: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我非常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比较好,另一方面根据商业理论完全能够证明经济增长到最后需要依靠投资。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专家认为我们应该通过鼓励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达到经济平衡,不过根据危机后的经济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要实现持续的、稳健的、平衡的增长,到最后还是需要依靠投资,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我现在正担心度的问题,尤其我们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有点过度。为了绕开马六甲海峡问题,我们在海外修筑了很多条战略通道,这些战略通道有没有考虑到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有没有考虑到未来地缘政治上的演变情况?我们经常和印度合作投资基础设施,不过印度制造业发展起来了,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并且随着全球经济出现变化,如果我们判断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不再出现金融危机之前那种巅峰的状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开采矿产、购买油田,从战略上、从财务上到底存在多少可行性?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更加谨慎一点。
关于多边贸易体系。现在新的贸易规则与WTO的规则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中美之间的BIT,现在正在进行的TPP、TTIP,还有个别领域的GPA、服务贸易,明显与WTO的规则不一样。这一体系是一个更好的自由贸易区,而WTO的规则将不可能再适用,甚至我们是不是要倡导一种新型全球化。那么,我们必须界定传统的全球化的定义。在2007、2008年以前高速增长时期的全球化,可以界定为中心外围的、放任的、没有监管的全球化,甚至是没有考虑到可持续性的全球化;2007、2008年之后传统的全球化出现了的倒退。若我们现在不希望它倒退,但又不能恢复到2007、2008年之前的繁荣,就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这也可以理解成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那么,新型的全球化应该是怎样的?它不是当年南方国家主张的那种完全革命性的、巅峰性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分享利益的全球化。
查道炯:什么是战略?为什么我们要参与G20的相关事务,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究竟我们是该推动、促进G20的发展,还是应该阻挡它的发展?其实无论是G20,还是G8+5,或是其他机制,对于中国来讲,战略收益是动态的。动态是指对外经济政策的可行度,需要共同商讨决定。如果我们不参与到G20中,那么很多事情有可能会有很大的阻力;而如果我们参与到G20中,那么,我们至少能做到知己知彼,从而有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设有G20研究中心,它是由财政部副部长领衔成立的。与中国一样,该研究所也对G20的定义、澳洲应采取的战略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希望这个课题不是一次性的课题,未来还需要深入展开这方面的研究,这是我们相互教育、相互学习的过程。
针对刚才何帆讲到的马六甲海峡问题,我认为马六甲困局根本不存在,只是我们自身经不起外界的恐吓而引发的困局。如果对方真心想炸毁我方的油、气、矿产,没必要等到马六甲海峡再下手。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恐怖主义,如果他们在马六甲海峡击沉了我国的商船,不仅得罪了中国,还得罪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所以,马六甲威胁其实并不存在。同样,中缅油气管道问题亦是如此。我觉得我们的很多战略并不符合常识,但是在国内这些战略的说服力却特别强,从而导致了我国在外交上长期存在很大的被动。因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判断力,不能完全受外界因素影响。
关于基础设施投资,我们要倡导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在实施过程中,要协调亚行和东盟的经济一体化。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那些鼓吹“国外扼杀中国”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要避免“中国阴谋论”这一说法。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各种输油管道线路都是一些浪费资源大搞战略通道建设的工程。我觉得基础设施投资固然重要,但是必须协调好既有的国际机制,避免做出不必要的战略投资。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