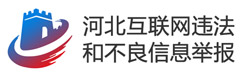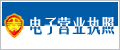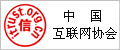欧央行前行长:央行不能替代政府和私有部门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浏览:次|评论:0条 [收藏] [评论]
2011年11月1日,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担任欧央行(ECB)行长八年之久后卸任。他上任伊始的2003年,正逢欧元区蒸蒸日上,而他离开之际,却是市场极度动荡、欧元区风雨飘摇之时。…
事实上,1993年即担任法兰西银行行长的特里谢,一直站在欧洲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舞台中央。2012年4月,他被任命为欧洲著名智库Bruegal主席。
不久前,在法国巴黎罗浮宫附近低调奢华的办公室里,特里谢接受了第一财经电视和《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联合专访。今年70岁的他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目光坚毅。他说他爱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并被波德莱尔的诗句所打动。
尽管已经退休,但特里谢依旧心系处于危机“震中”的欧元区。他认为,过去一年中,欧央行在现任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领导下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他一再强调,央行无法替代政府,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承担起责任,纠正国内经济失衡,解决欧元区内部不断扩大的“异质性”,并在中长期内加快经济和财政联邦化进程。
对于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的未来,特里谢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在确信人民币会成为全球主要货币之余,他给中国经济开出了八字箴言:“保持平衡,警惕泡沫。”
欧央行的决策是正确的
第一财经日报: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你一直战斗在风暴的中心,而今,你不用再担任欧央行行长了,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特里谢:虽然我的身体不再掌管欧央行,但我的心还留在金融危机里。我还心系危机“震中”――欧洲各主权国家。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
日报:你如何评价你离任后欧央行的表现?你认为这些措施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危机?
特里谢:我们必须承认,所有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英国、欧洲,尤其是欧元区,都处在非同一般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正视现状,尽可能做出明晰的判断,并且有所行动。
如果我们看一下央行的应对手段,一些央行推出了非常规政策,尽管不尽相同,但主要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类似行动。由于市场机制不再像危机前那样运行良好,你必须确保让这些货币政策能正确传导到实体经济。美国和欧洲的情况虽不同,但都面临市场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所以央行就要注意如何正确将货币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虽然我已离任,但我认为欧央行采取的政策决定是正确的。
日报:我有一位金融家朋友说,如果要选一位意大利人做欧央行行长,那么只有德拉吉是合适的;如果要选法国人做欧央行行长,那么候选人会有好几位。你认为你和德拉吉在方法论、做事风格和理念方面有什么不同?
特里谢:在理念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都在做欧洲民主机制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即维持物价稳定和机构稳健,这是市场信心和稳定的关键;当然,我们也有不同之处,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共同合作,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朋友们一起谈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充满信心且高效率地为欧元事业努力。
在我做行长时,德拉吉也是理事会(欧央行的决策机构)成员之一,当时的政策决定也是所有理事会成员的共同决策,因此在德拉吉就任行长后有着连贯性。但由于危机随时都在变化和发展,无论是欧洲还是全球形势都今非昔比,所以必须尽可能直面现实,传达清晰的政策。因此,从总体和长期目标来看,我不认为我们存在任何差异。即使有所不同,那也是因为欧洲和全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变化。我要表达的主要信息是,这不单是欧洲的危机,也是全球的危机。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爆发那样,彼时震中在美国,而此刻震中在欧洲。
日报:你担任欧央行行长时,和理事会成员魏德曼(Jens Weidmann)有什么不同观点?
特里谢:你知道我们有理事会,正如英国、美国和日本一样,理事会成员的意见不尽相同。在理事会内部,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声音。在英国、美国和日本,公布的决策中会披露谁投了赞成票,谁投了反对票。但和这些央行不一样的是,欧央行一直以来都认为,我们有17个国家的成员,我们希望一旦做出决定,大家都必须对外一致,无论其中已经权衡了多少利弊。我更喜欢这个主意,尤其是当我们正在应对这场可能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时。
日报:事实上,你开启了欧央行历史上的非常规措施,但之后你似乎并不愿采取更大胆行动。一些批评人士称,这是你的过错,而德拉吉愿意在恰当时机采取更大胆行动。你认为这种评价是否公允?
特里谢:这些说法主要针对我在任时采取的购债行动。我不得不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无论在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央行不能代替政府,这意味着政府的调整是绝对必需的,这是一切恢复稳定的关键。而这些国家也要承担起共同责任,确保陷入困境的国家遵守条件,同时在有需要时能获得贷款。这是我在任时经常传递的信息,据我所知,欧央行在这方面也保持了连贯性。欧央行一贯的态度是,我们在必要时,在必要的地方,能够采取迅速而大胆的行动,但我们不能代替政府承担其自身及共同需要担负的根本责任。
日报:欧央行和EFSF/ESM似乎在购债问题上形成了分工,欧央行只能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无论是直接货币交易(OMT)还是证券市场计划(SMP);而EFSF和ESM则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你认为最终这三者可能合为一体吗?
特里谢:不,我认为不该结合。这其中是很有理由的,尤其是欧央行只能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券。在我看来,在一级市场购买主权国家债务是不符合央行职责的。我们从来不干预一级市场。在欧盟条约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仅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干预二级市场,但同时政府本身必须负起改革的责任。你知道,那时我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就提出了强烈要求,他们必须表示出完成必要改革的严肃决心。
日报:如果EFSF和ESM可以拿到银行执照,那就意味着它们可以向欧央行借钱,再用这些钱去投资一级市场,这会有什么区别?
特里谢:准确地说,欧央行不可能为后两者提供融资,在我管理的时期就行不通,因为这会带来许多显而易见的麻烦。
加速经济与财政联邦化
日报:你去年提到了欧元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认为欧元区内部的异质性还不及美国各州之间那么大。但目前看来,欧元区各国之间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大,在欧央行宣布OMT之前,南北欧之间各国的融资成本也已大幅拉开。你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吗?
特里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看一下欧元在诞生后的第五、第六年,当时的批评说德国增长不够快,而南欧国家却增长迅速,欧元区各国存在太大的异质性,应该怎么办?我的答案是,德国正在重获竞争力,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正在见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德国增长迅速,但南欧国家不得不进行改革,因为经济失衡,所以要调整的是它们。
如果消极地看,欧元区总是处在失衡之中,德国增长不是太慢就是太快,但这恰恰就是欧洲大陆前进的方式,或多或少总会需要再平衡的过程,这是必需的。虽然美国各州也存在差异,但他们已经取得了政治和财政联邦化,因此情况和我们完全不同。对欧洲而言,最核心的是,不仅要将正在进行中的调整进行到底,而且我认为,中长期内,欧元区要进一步加快经济与财政联邦化的进程。
日报:对此我们已经采取了各种短期措施,那么你是否认为这种“异质性”在中期内能有所减轻?
特里谢:一些国家的利率攀升非常快,爱尔兰和希腊都是如此。但他们正在调整和修正这一轨迹,尤其是爱尔兰到目前为止做得很出色。你要知道,失衡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行纠正。这种纠正现在正在发生。未来我们必须要避免的是欧元区内部出现太大失衡。而这要求非常严格地执行《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及财政自律,并且你要有一个坚实的支柱来评估各国竞争力和单位劳动力成本。我相信,从长期看来,这会是经济和财政联邦化的开始。
日报:我们希望出问题的国家能够重建韧性。但当我们看待“异质性”时,也有人认为分化(Divergence)是另一种方向,并将成为“欧洲联邦共和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替代物。例如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券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来购买,因为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更加了解,因此对政府财政预算有更大约束,你认为这可行吗?
特里谢:在任何情况下,要想那么做,一个特定国家必须有适当的储蓄,所以需要对经常账户失衡做出修正,需要一个平衡的经常账户,有自行融资的可能性,有自己的经济和财政预算。所以无论以何种方式,所有失衡的国家最终都必须做出调整。
关于分化和重新国有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在全球层面上观察到的现象。在金融领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很多国家的金融部门都已出现重新国有化的趋势。在一些发达经济体,纳税人被要求帮助拯救银行体系,这引起了一些情绪。
在欧洲,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当然这有悖于单一市场,过去五六十年以来整个欧洲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单一市场,不仅是单一货币,更是单一市场。这就是为何银行业联盟如此重要,因为至少在金融领域支持单一市场,而不是分裂和重新国有化。所以我相信欧洲今天有更充分的理由来实现单一货币的单一市场。
二战后的类似参照是美国,欧洲的单一市场或多或少是受美国的影响开始建立的。但今天有中国,有印度,明天还有巴西、印度尼西亚,欧洲正处在一个非常庞大的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群体中,不光是美国,还有很多别的国家。我相信,今天的我们比二战后有更多理由来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
日报:这可能是最理想的情景。但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变成现实,或回到之前谈到的“异质性”问题,一些国家是否会实行短期的资本管制?例如欧元还是存在,但在短时期内一些国家会通过分裂的市场来应对危机。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在危机的某一阶段出现?
特里谢:我认为这将是为了走出现状而出现的最坏情形之一。正确和适当的方法是维持最根本的原则,即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不只是在欧元区内部,而是对欧盟27个成员国的原则。当然,只有你进行调整才能奏效。你必须对自己的经济做足功课,让资本没有外逃的倾向,确保一切都在正确的方向上。这就是为何欧央行如今强烈呼吁要求进行调整。做你应该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些过去做出正确行动的国家,正是今天在危机中表现出韧性且还在危机中继续增长的国家。所以对财政支出和预算进行良好管理是必要的。
单一监管机制无损ECB独立
日报:欧元区目前在谈论银行业联盟的问题,包括欧央行将可能监督欧元区的每一家银行。对此你如何评价?
特里谢:欧元区政府决定让EFSF和ESM能够直接对欧洲银行业进行注资,而不用经由国家,这是正确的决定。这对于让主权信用和银行信用“脱钩”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如果国家和银行之间有100%关联度的话,就会导致恶性循环。能够理解的说法,如果要对银行注资,就必须拥有统一的监督机制,这个监督机制必须在整个欧元区得到执行,而非国家层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即可以直接注资,但其前提必须是泛欧洲的单一监管机制。
很明显,欧央行是可以承担这项职责的机构,这是欧盟条约允许的,欧央行可以这么做,只要全体成员一致通过且与条约不冲突。现在的一个争论是关于是否该只关注大型机构,还是全盘兼顾。我个人偏向于专注于系统性大型机构,这可能更合理。但可能注资对象不是那些仍被国家权力机构监管的银行。这里有一些矛盾。
日报:对。但你觉得这一新的监管职责是否会损害欧央行的独立性?
特里谢:不,我不这样认为。在一些已经引入相关机制的国家央行里并没观察到这种情况。而且,在关注中长期内物价稳定的欧央行理事会和承担监管职责的部门之间会有适当隔离。他们的员工可以非常接近,但这两个部门间不应产生混淆。英国也正在践行这一理念,他们的央行也有同样隔离,法国也是。你还可以看到美国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是我们解决系统性威胁的办法。
日报:欧元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吗?
特里谢:从2007年8月9日以来我就一直被问到这个问题!五年多了,我总是说,这是个过程。未来不是注定的,而要靠我们自己来书写。我们所有人必须要负起沉甸甸的责任。如果我们各司其职,那就为更好的未来铺平了道路。但我们仍处在一个极具挑战的处境中,如果不这么认为就大错特错了。欧洲是全球主权信用风险的震中,但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鉴于这些发达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其他地方,全球经济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和挑战,这就要求每个国家都要努力加强自身韧性。这是我所说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就是韧性。
日报:另一个问题就是逃往安全资产的趋势。我们看到美国和德国的国债收益率已降到历史低点。德国和美国这样极低的收益率,会对整体金融市场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
特里谢:这种状况当然是不正常的。自危机开始以来,世界主要央行纷纷采取非常规措施,因为他们担忧金融市场无法正常运转。现在的不正常状况包括你观察到的极低利率,另一个就是极高的利率,这两种情况都是不正常的。这两者再次证明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不仅在欧洲层面,而且在全球层面,去修正不平衡,修正这种不正常情况。
我测算了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由于采取非常规措施而导致的资产负债表增长。可以看到,在日本、美国、欧洲和英国,这一增幅超过了GDP的10%,在一些国家更高。日本的措施开始得更早,因为日本有自己的危机。那时别的发达经济体看日本,认为他们只是特例,但后来人们意识到情况要复杂得多。日本只是提前经历了一些不久之后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经历的情况。所以,我要传递的信息之一就是,每个国家的央行必须说,我们正在做不寻常的事情,但你们自己必须去纠正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不能替代政府,也不能替代私有部门,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市场完成其应该发挥的中介作用。全球层面的所有央行都必须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给G20国家的政府。
日报:你刚才指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央行对全球经济注入的大量流动性。你是否担心这种流动性无法在危机结束时及时撤回,从而导致恶性通胀?
特里谢:我认为无论如何,当时机来临时,流动性必须要被撤回。因为非常规措施一定要与观察到的市场失灵程度相称。所以如果市场回到了正常情况,那么就要马上减少非常规措施,最终完全停止。这就是欧央行一直在做的事情。在我任期内,我们在一些特定时刻,废止了一年期的LTRO(长期再融资操作)和六个月的LTRO。我们总是根据观察到的市场失灵程度来进行调整。所以说,要确保你在一切恢复正常时能撤回流动性,这也是最终目标。在这个方面,如果央行层面非常警惕,我相信能够保持精准,不会再次制造问题。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做出判断,确保在任何时候不做过头。
日报:你认为两轮LTRO不算太多吗?
特里谢:不,我不这样认为。看一下市场情况,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处境。而且欧央行在必要时也有能力将注入的流动性抽回。你知道,我们有一切必要工具去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欧洲的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在必要时及时撤回流动性,从技术上说这是完全能做到的。问题在于,确保其他各方能做好它们的分内事。各国政府自身努力并且携手合作,还有私有部门,因为很多改进都必须来自私有部门。
人民币会成为全球主要货币
日报:你指出了发达经济体的关键弊病。那你对新兴市场是不是更乐观一些?
特里谢:新兴经济体从危机开始时就展现出韧性,已经超过五年时间。为什么他们能做得这么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曾经经历过危机: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亚都出过问题。这很清楚地说明,在经过调整后,你才能保护自己免于遭受新的危机,你就更具有韧性。但就像我刚才所说,在全球层面上我们仍在经历全球经济失灵的不正常情况。这对于G20国家来说是个问题。没有国家应该认为自己和所有其他国家之间是互相独立的,我们互相依存。当亚洲发生问题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而现在发达经济体产生问题,我们也都会受到影响。
日报:欧元就像是一个梦,我们都想要去珍视和实现。但同时我们还有美元,当欧元面临困难时,美元似乎承载了过度的特权。在这个时候人民币也许能扮演一些角色。你认为人民币是否有可能在未来十年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特里谢:首先,对于欧元,我们要看到一个区别,即货币本身和欧元区金融稳定是不同的问题。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和主权信用出现了问题,但欧元却非常坚挺,欧元极具韧性。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在欧元建立之初是1∶1.7,再看看今天的汇率,欧元一直都相当稳定。作为货币本身,欧元受到了很好的基本面支撑。我们15年来都维持着稳定的通胀率,欧元区的经常账户是平衡的,大多数欧元国家都是如此。
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进步和成功是如此巨大,所以在时机成熟时,人民币会成为全球性货币。这当然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意愿,也要求加强汇率灵活性,从而才能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这也取决于中国持续的成功,对此我非常确信。在1982~1983年我自己曾有幸与中国政府就一份关于保护和发展互惠投资的协定进行过磋商,当时我曾几次造访北京,惊讶于我们完全处在不同的世界!但再看今天的中国,你会看到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功奇迹,完完全全地令人惊叹。我确信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水平都会得以持续提升。
日报:人民币成为下一个全球性货币是否面临着一些风险?
特里谢:我相信当一个国家及其经济运行如此良好和稳定,其货币一定会成为全球主要货币。当然这里面还包含一些责任,这些责任是不能逃避的。这也要求中国强化好的政策,而不是安于现状,那样会加剧失衡。不只在中国,在全世界也一样。
日报:你希望向中国的领导层传递怎样的信息?
特里谢:对我来说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有些过于大胆了。但我要说,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自己见证了这一过程。我认为在金融和经济领域会有很多新的挑战来临,而不平衡问题也一直会是威胁。所以我只能说,我观察到的中国央行正在实行的货币政策非常好。当然,当一个经济体快速增长时,可能会或多或少存在泡沫。我们也看到了泡沫破裂时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所以要非常小心地关注。在我看来,中国领导层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继续坚持这条胜利之路吧,保持平衡,警惕泡沫――这在我看来,是最最关键的。
日报:今年4月,你说你的枕边书是《记忆的艺术》(The Art of Memory)。你现在读什么书呢?
特里谢:枕边书就是你值得一直反复读下去的书。我现在还在读一些诗歌。我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特别偏爱。这是了不起的诗作。还有一些短诗、十四行诗。我还很受波德莱尔诗作的打动。因为这帮助你回到本真的层面。这在我看来非常重要,通过这些诗看到很多亘古不变的东西,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我喜欢抓住转瞬即逝的感觉和情绪。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首页
首页